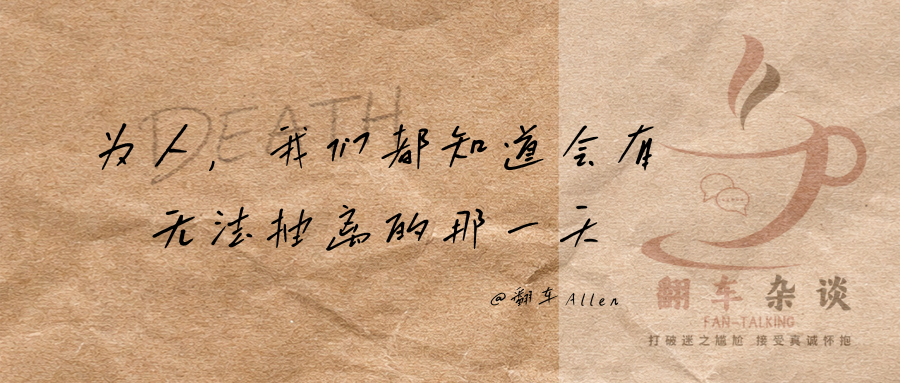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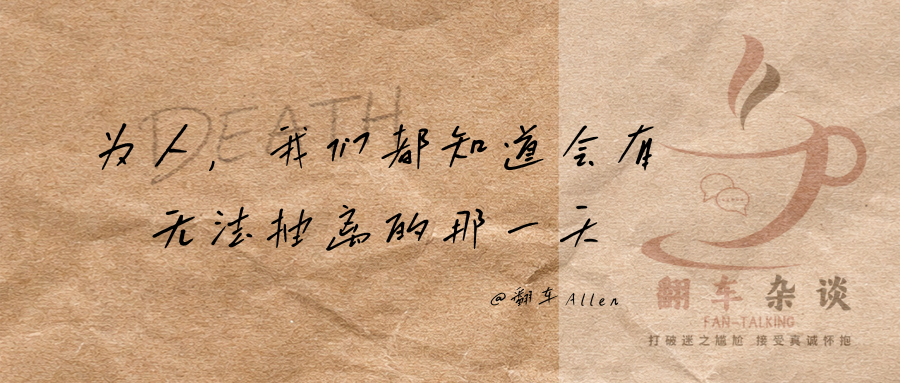
(原封面奉上)
那日闲晨,置顶着一个不冷不热的天。老婆孩子们还没起,我与母亲坐在餐桌前,她在等候厨房里的鸡蛋煮开,我在喝水。
最开始,我向她表达了自己较少回乡看望老人的挂怀之情,然后询问老人身体健康情况——这是母亲的生活惯例,每天晚上都会给远在家乡的外公外婆打一通电话。加上最近这段时间,她刚刚从乡下返回家中。
母亲坦言:你外公还是那个样子,过一会儿就记不住人。现在吃得少了,睡得也多了,在厕所一坐就是半个小时;外婆就稍好一点,就是看着一直很瘦。
接着,我头脑一热,赌上可能被降责的风险,问了母亲一个问题:
面对双双九十多高龄的父母,你的心理准备过那天会到来吗?
死亡教育的忽然凝视,是一个家庭几代人的言语禁区
母亲似乎不打算回避我的话题,她坦言自己其实想过数十遍:她最害怕的就是夜半时分那让人警觉的电话,说会怎么打来,家里的消息怎么开口,亲戚该怎么通知,家宅变灵堂那天会不会下雨,自己在奈何桥下跪着送别会不会哭到力竭……
她说到最后,声音很平,但眼眶的颤动和晶莹的躲闪没有藏住。
她说那天要是真的来了,想想还是会很悲痛;然后就是下葬的时候,还是会很伤心;再往后,是自己的戒断反应。不是一直难过,而是无意触碰往昔带来的阵痛,像身体里有个开关,隔三差五被按一下。
她讲这些的时候很平静。平静到让我意识到,所谓心理建设,大概也只能做到这里:你可以提前知道它会来,但你没办法提前把它变轻。
我们这一代人,其实挺擅长做心理建设的。刷到谁家老人走了,会顺手在回应区打上三只白蜡烛;看到一句亲人失去时写得走心的慰问语,也会默默记下来。像是把道理和形式存进脑子里,等哪天用得上。可道理和形式这两样东西,平日不拿出来的时候都很完整。
而失去不是。
失去是一种关系突然断掉,你站在原地,伸手去触摸,然后摸到苍白与无措。
我对死亡的很多理解,大多来自见闻的旁观:来自医院走廊的熄灭的红灯;来自亲戚之间压低哭腔的声音;来自那些我不属于其中,却完整看过结尾的场面。
我们几代人谈过同一个问题:人走到最后之前要不要插管。
老一辈人说得很直接。到那个程度,就别折腾了。医院插管、手术抢救、药物维持,在他们眼里不像多活几天,更不是生命延续,而是尊严受罪,以至于到弥留之际都不能体面地走;
中间那一代,就是我们父母的理解。不管怎么样都不能看着亲人逝去,如果医术和科学能够延续他们的生命,自己作为子女是一定要让他们在人间多留几日的。因为眼看失去只是时间问题,而自己真的还没有做好那种准备;
我们这一代反而更容易条件反射地拒绝“不救”。不是因为更懂生命,而是更怕承担那个动作——放手。
歌手薛之谦在演唱歌曲《农民与土地》中有这样一句词:“这一生的牵挂/两场疾病就讲完了”
所以,那个时候的插管不是为了赢得与病魔的抗争,只是为了把对他人的告别往后挪一点。哪怕只是一周或者一天,心里也好受一点。虽然存在着代际差异,但三代人的动机,其实都是想让正在面临死亡威胁的人,尽量少背上“插或不插、拔或不拔”带来的额外痛苦。
我得在这里讲清楚一件事。我并没有听到什么死讯。这篇文字,也不是在谁出事之后才写出来的。恰恰相反,是因为什么都还没发生,我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:自己接收到的生死教育还是太少了。不是我不去想,而是从小到大,这个话题几乎没有被认真放进生活里。几代人的观念积弱,加上避谶的顽固,让死亡教育变成了一件只能在“痛定思痛”才被允许讨论的事。
可问题是,它迟早要来。
当一个人生必考课题长期被绕开,上一代人不让预习,只得偷偷自己学肤浅的概念或零碎的大纲,少有铭心的实操经历和走心的渗透过程,它就会在真正出现时变成一块自己的技能空白。你不是不在乎,你只是没学过怎么面对。于是等它就这样仓促叩开自己的心门,你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应对:慌、乱、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,甚至用“我不相信,再说一次”来换取一点点心理缓冲。
我后来才意识到,我问母亲的那个问题,其实不只是问她。
我是在问自己:我到底有没有资格说,我准备过。
硬要说,细想下来也是有的。
去年那次火灾逃生之后,我当晚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我毫无准备地成了真正的一家之主。我的父母不知所踪。没有很戏剧的场面,他们就是突然不在了,得不到解释,永远留下了这个未填的坑。于是乎,家里所有事情一下子落到我身上。要我决定,要我安排,要我应对,要我撑住。在那些独自顶着压力硬撑着的夜里,没有人安慰我,也没有人催我成熟,只有一种很荒凉的现实感:就是这样,突然轮到自己了。
梦醒神清之后,我才慢慢缓过劲来,认识到并非自己不会做事,而是突然发现,我对父母的依赖并没有拔除干净。我以为自己成年了,工作了,成家了,就已经具备完全独立的资本了,可那个位置一空出来,我才明白很多所谓独立,其实只是因为他们还在,无论是社会意义还是精神意义的双重存在。
父母还能为自己无言地撑着,本身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不是奢侈在他们能替我做什么,而是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天然站在我这边的位置。
而那个梦映射给我的创伤也没有就此结束。它顺带给了我创作灵感。后面两个星期,我反复构思一部并不存在的小说,名字叫《东山》。我不想为它设定什么宏大情节。可能故事写的只是:上一代的掌权者突然缺席,下一代一个人被迫承接全部。主人公的故事不是热血成长,而是没准备好就被推上去,边见边学,边撑边错。这个故事的内核已经显现,也曾跟好友谈起,“这是我今年的重点之一”,但关于正文的开篇,眼看新年一月已入下旬,我却迟迟没有动笔。
所以母亲说戒断反应,我一下就懂了。
那不是单纯的难过,而是关系断掉之后,身体和情绪还在反复确认:真的没有退路了吗?
你会在某个瞬间下意识想求助,手机拿起来才想起对方不在了;
你会在某些日子突然泄气,连原因都懒得解释;
你会被一句很普通的话刺到,像旧伤磕到冷水。
理性当然知道结局已经发生,可感性的习惯和依赖跟不上。它们需要时间慢慢退潮。
那心理建设到底有没有用?
如果你指望它让你那天镇定、体面、像个成熟的大人,那多半会失望。很多人都会翻车。会哭得难看,说话混乱,甚至想逃,都很正常。它真正能用上的地方,往往不在那天,而在之后;它可能帮你少一层自责,少一句“我怎么还没好”;它不替你挡痛,只是提醒你:这不是异常。你没有走错,你只是在告别。
为人这件事,说到底就是这样。
面对死亡,你明知道会有无法抽离的那一天,但你依然会依赖,依然会舍不得,依然会在某个夜里被一种很沉的东西控住情绪。
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有两件事:
他们还在的时候,别太糊弄;
他们不在之后,允许自己慢慢戒断。
至于那一天什么时候来——
没人知道。
但至少现在,这个缺失的人生课题,也将会在遥远的以后,被我一点一点领悟。
2026年1月20日 16:03







